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13
顾准的思想没有过时

顾准1965年在长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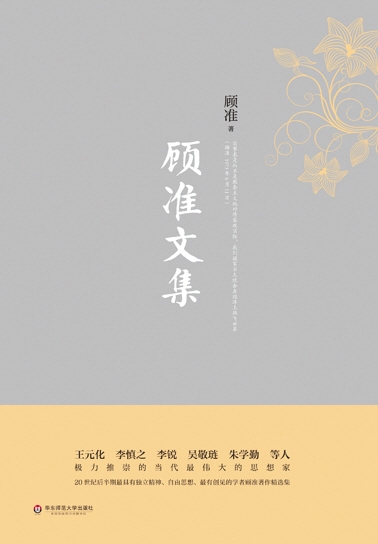
《顾准文集》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年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版的《顾准文集》。

在顾准逝世40年,《顾准文集》出版20年之后,我们需要明晰,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时过境迁之后,怎样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40年前,顾准离我们而去。
18年之后,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面世。此时,中国在一场风波之后,正被是否把改革开放坚持进行下去的争论所纠缠和困扰,“姓社姓资”的质疑来势汹汹,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甚嚣尘上,如何看待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左的倾向和路线,如何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都成了争论不止,需要整个国家作出何去何从选择的大问题。顾准的遗著,他的思想、苦难经历和道德形象,成为中国人审视过去、选择未来的启示和精神源泉。
顾准的经历、遭遇和思想引起中国读书界、学术界、思想界的震动与共鸣,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面世之后10多年间,更多的顾准遗著,他的日记、传记,对于他的缅怀记忆和研究的书籍不断问世,顾准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一面旗帜,他的论述是当代中国思想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在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方面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甚至难能可贵的突破,其中就蕴含了顾准的启发和提示。
在尊重和崇敬的同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明白,顾准是人不是神,不应该把顾准供奉为新的理论菩萨。一些对顾准的经历和思想有研究、有思考的人对他的观点也发表了不同意或补充性意见,他在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各个方面的观点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发挥,他的个人悲剧放到了时代悲剧背景中理解和考察,他的前瞻性观点不时被人们提起。
今年是顾准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要问,曾经被人们热烈谈论、广泛讨论的顾准及其思想,在经历了20来年岁月的淘洗之后,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立足之地吗?这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国势变化,我们已经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用新的眼光和标准来看,顾准及其思想还有价值,还有意义吗?如果有,那价值和意义何在?我们还可以问,顾准需不需要超越,如果需要,应该在哪些问题、哪些观点超越?
直面问题的道德勇气
首先,我们要肯定,顾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伟大祖国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学习。
顾准中年遭遇厄运,从高官变为罪人,妻子自杀,子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兄弟在远方不得相见,老母亲近在咫尺也不能见面,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自己则身患绝症、衣食不全。而在这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再加上“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恐怖气氛,像顾准这样的人想自保都困难,但他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发愤读书、思考、研究、写作。他一心想要揭示的,是“中国何以至此”的谜底,他全力想勾画的,是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一个人,在自顾不暇的境况下,心中牵挂的,是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这是何等地难能可贵!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是中国士人古已有之的一种高贵传统。就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动情描述的那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是需要有一些伟大的心灵来充实和代表其伟大传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哥白尼、布鲁诺,在现代美国,有马丁·路德·金,在古代中国,有司马迁等,在当代中国有谁呢?幸好,我们有顾准。顾准的存在表明,即使在“全面专政”、是非颠倒的“文革”时代,中国人的勇气和良知也没有丧失殆尽,即使在煽动狂热和迷行的“文革”时代,中国人中间仍然有头脑清明者。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阵痛的,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和方向的迷茫,顾准是激励我们坚持理想的一个坐标。道德勇气,这是顾准遗留给我们的第一笔精神遗产。
经济思想影响深远
顾准在思想上学术上的首要突破,表达在他于195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排除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会起作用。这些提法虽然还不等于肯定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却是朝这个方向探索的第一步——事实上,在顾准另外的手稿中,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实际上,在发表这一论文之前,顾准就用自己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想影响过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后者把受启发后形成的观点发表在1956年第6期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领域存在多么坚固的理论堡垒,有多少经典著作和导师语录像紧箍咒一样使人动弹不得,我们就知道顾准发表上述观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改革开放到来的年代,通过孙冶方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肯定价值规律的涓涓细流终于逐渐汇聚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大潮。
今天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顾准当年的设想,但市场的不规范,受到权力干预和扭曲的程度,更是当年顾准完全想不到的。贪污、贿赂、腐败横行,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社会不能忍受的地步。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作为顾准学生或同行的经济学家,也包括对权力垄断和滥用抱警惕态度的法学家——大声疾呼,强调市场经济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市场必须公平和规范。这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我们看到,不但顾准的主张得到继承,他的精神也得到发扬。我们坚信,秉承顾准的精神,他说过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他没有说过的东西也可以经过我们的探索与研究得到。顾准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可以简单归纳为两条,一是正视中国的现实,二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许多顾准思想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那句著名的话“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顾准强调这句话对于100多年来有过难堪与屈辱经历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要了解顾准的深意,我们可以继续读马克思紧接着的话:“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阻碍我们发展的,主要不是那些所谓后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复旧的可能性和危险始终很大。在中国,前进一步往往困难,需要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倒退却可能在一夜就完成。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总算可以彻底告别那些陈旧的事物,一提到过去经历的那些可笑、荒谬东西,人们通常用一句话来打发:“都什么年代了!”但是,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旧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就像我们在薄熙来、周永康的言行、政策和做法中看到的那样。通观顾准的著作,他始终都在关注与批判那些以新面貌伪装的旧事物,在这方面,顾准的思想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追求真理矢志不移
顾准把他苦苦思索、欲求解决的问题表达为“娜拉走后怎样?”这是说,人们当初起来革命,是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幸福,但是,革命胜利了,目的却没有达到,甚至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革命所欲建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顾准举目观望十月革命成功几十年之后的苏联,看到的是大搞军备竞赛,穷兵黩武,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群众的意见受到压制。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如果在固有的学说中找不到答案,那么能不能放眼世界,放眼历史,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一些道理?顾准为此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力图理清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他在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时,显示了他那宽阔的目光和深刻的睿智。顾准为回答这个大问题打开了重要的思路,对此有些人会认为非常超前甚至过于超前,另一些人会认为那不过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怎样说,新的思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顾准在其中所做贡献的份额可以不去争论,而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还要靠我们这些后来者,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还需要寄希望于后代。
顾准的高尚和不平凡在于,他曾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场革命,作为胜利者和有功者,他曾经享受高官厚禄,但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的初衷,他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事业上都置身于一种传统之中,但他不是仅仅被这个传统带着走,而是不断地回到原点,用当初的目的和追求来衡量现状,用当初的理想来要求自己。
与顾准一样,我们要把这样的问题摊在自己面前: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
□薛立山
[新京报]
继承顾准:“中国问题”再审视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1965年9月,陈敏之给“五哥”顾准写了一首赠诗。其时,顾准已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紧接着,“文革”开始,狂风暴雨中,他在大字报上只写下两个字:读史。
从历史入手,落脚于现实,处处弥漫着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学者严肃思考、独省如灯的态度和身姿。顾准思考的问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如何看待、维护个人权利?发展科学民主的同时,怎样处理传统思想资源?这可以概括为“中国问题”,顾准的思考、写作莫不以此为依归,那么,近四十年来,它们是否有了进展、变化与更新?顾准前后的学者们又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无疑需要一再审视。
娜拉出走后
有人打着“改革”旗号掠夺大众
顾准: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么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吴敬琏传》)
吴敬琏: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顾准日记》序言)
经验主义
不应再有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
顾准: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九十年代反思录》)
个人权利
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
顾准: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天、天子压倒了一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顾准文存》)
哈耶克: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
徐友渔: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荷兰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重读自由主义及其它》)
传统思想与科学民主
批判之余,传统思想可创造性转化
顾准: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
林毓生: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实可以作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史官文化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
顾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顾准文集》)
波普尔:从来没有一个权威承认过,思想上大无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一类人。当然,权威们总是对他们鉴别创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们所指的创造性仅仅是快速领会他们的意图,他们永远不可能明白两者之间的不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罗志田: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核心地位,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样。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却不免有些夸大。历代史官的地位,实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不论我们把传统视作包袱还是资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责任,也不足以独揽其光荣。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传统者,不过人云亦云,似有些“说而不思则罔”。
(《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