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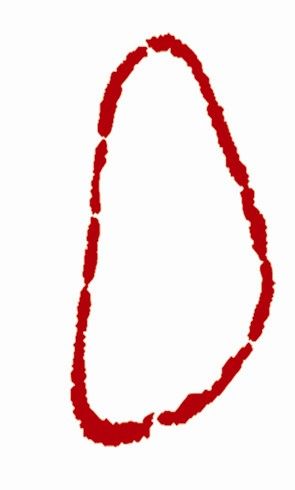


青铜器、车马坑、晋国历代国君墓葬……曾经名垂青史的晋国辉煌霸业,在晋国博物馆的展品中复活。而将这卷史书打开并解读的,是几代考古学家。上个世纪后半叶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当时在春秋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只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早期都城未找到。
晋国在春秋五霸中称霸150年,立国600多年,延续至今成为山西的代称。早期都城找不见,这是晋文化研究中的巨大缺陷。“找到晋国”对考古学界来说意义重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学家的目光越过中原大地,聚焦到晋南。“寻踪晋国”,这一找就是50多年。
从“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到晋国博物馆的建立,几代考古人的心血和汗水,使得晋、晋都、晋文化浮出水面。那个书本上的“晋国”逐渐清晰,来到我们眼前。
晋国博物馆·展示盗墓历史
在晋国博物馆,有一块展览内容是有关那段盗墓历史的,甚至在墓葬展示中,也没有人为消除盗墓痕迹,用专门的指示牌标记“盗洞”等痕迹。
这在国内博物馆中十分罕见。对此,晋国博物馆工程副总指挥、原曲沃县文物旅游管理中心主任孙永和说,“博物馆是记载历史、还原历史的地方,我们这么展示就是尊重历史,让人们痛恨盗墓分子。”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展示盗墓,非常忠实于历史,可以让观众看到考古多么不容易,保护文物,要克服恶劣的环境,这里面既包括野外的艰苦,也包括和盗墓来做斗争。”
一批“北大生”来到了曲村
晋国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面墙是用灯箱展示的“曲村——天马遗址”。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呈现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剪影,或蹲或趴或站,有的手拿探杆,有的手拿手铲。
现年77岁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伯谦谈起自己当年的样子,说,“没错,远看和农民没什么差别,就是一手一手地在地里挖、刨……”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规划,当时侯马一带有大批的工业项目要选址上马建设,国家文物局在侯马组织考古大会战,以免在工业建设时损毁文物。从1960年到1979年,考古人员在曲沃县与翼城县的交界处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并进行了两次挖掘,初步确定是周时期晋文化遗址。
李伯谦参与了其中的挖掘,他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考古领头专家邹衡先生一起对曲村遗址进行了挖掘,“当时发现了一些墓葬,我们也在私下探讨这是不是晋国的始封地,但还没有发现有明确铭文,我们有一个想法,在这里建设一个稳定的实习基地,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山西省文物部门的人员一起对此进行长期挖掘研究。”
这个方案很快就被通过了。1980年,第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曲村。由邹衡和李伯谦带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与北京大学的教师、学生共37人组成,考古挖掘从当年9月份进行到1981年春节前。
当年尚且闭塞的村子里来了这么一支队伍。村子里的村民不清楚这些操着京腔的外地人是干什么的,大家只是喊他们“北大生”。领着这群“北大生”的李伯谦第一个头疼的问题竟然是“生存”,他第一次来曲村时还带着介绍信,到公社去吃饭都不让,只能到村里农户家吃派饭。
看着介绍信,村里的队长很为难,“你们这也不是搞水利打井的,也不是来收税的,给我们这村里也没啥用,你们考古算做啥?”好说歹说,队长勉强同意接待,将李伯谦一行人安排到了一农户家,当时农户家里条件不好,并没有多少空房。李伯谦他们找到的这个房间前天刚刚办完丧事,这家的老太太去世了,所以留下了这间空房。
李伯谦回忆道,“房间是办事的房间,我们吃的饭是办事留下来的馍,门上还贴着白,第一个晚上,我们4个大男人都不敢睡觉,打了一晚上扑克。”
就这样,考古工作开始了,考古人员租住着村民的农房,自己生火起灶。从1980年到1990年,7批考古人员陆续来到曲村,村里还建起了考古工作站。在考古学家邹衡的带领下,大家发掘出大批墓葬。邹衡当时断言,这就是晋国的始封地和早期都城所在地,但因缺少大型宫殿基址和诸侯陵墓等相关证据,在当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晋侯踪影到底在哪里
晋国博物馆的“发掘史”长廊展厅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个老人,坐着竹椅,手拿钢笔,认真在写东西。来到这里的观众刚开始都会很诧异,怎么有个人“坐”在这里一动不动,走近一看,原来是座蜡像,蜡像的原型正是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
这座蜡像勾起了很多考古人员的回忆,它的审定人,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田建文正是邹衡老师的学生。1982年,还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就读的田建文,跟随邹衡老师第一次来到了曲村。正是那次实习,让他的一生也和晋侯墓地扯上了联系。
田建文回忆,邹衡老师和考古人员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找到“晋国始封地”。邹先生甚至断言就在此,但从1980年到1990年考古发现一直没有直接证据,到了1990年,邹衡先生已经60多岁,面临退休,十年的曲村考古要有个总结,他开始着手撰写《曲村——天马》考察报告。
1991年春节,忙于工作的邹衡先生决定在曲村过年,抓紧时间整理报告。大雪封路,时年64岁的邹衡在曲村的考古工作站中一字一句审定着他编写的曲村考古报告,同行的李伯谦也没有回家过年,在此一起工作。大年初五,他的弟子、当时已是北大教师的刘绪从北京赶到了曲沃,找到了已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班的田建文,一起乘坐考古所唯一的一辆货车来到了曲村,没几天,又有几个弟子冒雪赶来。那个春节,考古队员又这么相聚在曲村。
欢乐、激动之外,邹衡先生谈到了当时已经日益猖獗的盗墓,田建文常听到邹衡先生说,昨晚听到爆炸声了,看来又有墓葬被盗了。
盗墓渐猖獗曲村遗址请求保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琨璋同样是邹衡的弟子,他于1984年到曲村进行发掘实习并负责2002年之后的晋侯墓地考古挖掘工作。他回忆,自己刚到曲村的那几年,村民对考古一无所知,考古队发掘回来的东西就放在屋里,有的青铜器有锈,就和老乡借一个缸,用当地的米醋泡着放在院子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对房东来说,你可以住房子,但不要把发掘到的东西带回家,那时候当地人对墓葬里的东西有一些忌讳。”吉琨璋回忆。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盗墓之风盛起,当地派出所只能是做到把大家往回赶,考古队无奈,只好动用考古经费请求当地公安部门派人来值守。
李伯谦回忆,“隔段时间一来,就发现村里有盖新房子的,有人就说这是靠地下的东西发财的。”有一次,公安局抓到了盗墓贼,李伯谦和几个考古人员申请要见一见这些人,当面问一下为什么要盗墓。结果一看,竟然是自己租住房子旁边的邻居。这让李伯谦十分痛心,从忌讳墓葬,敬畏祖先到利欲熏心,疯狂掘墓,仅仅数年。
考古人员的无助感来自各方面。李伯谦回忆,当时县里有官员就盗墓责备考古人员,“你们不来,你们不雇用这些民工,能有盗墓吗?你们培训他们帮你们考古,他们会了,就盗墓了,源头还是你们……”另外,盗墓犯罪组织与官员勾结,即便是有公安人员值守,古墓也仍然被盗。
从1989年开始,文物相关部门开始向省政府、国家文物局打报告,就盗墓事件请求保护。1989年6月,李伯谦代表北京大学考古系给国家文物局致函,要求对“曲村遗址”进行保护。1990年3月,北京大学又向国家文物局致函,再次要求“紧急保护曲村遗址”,但都没有回应。几个月后,同年麦收前,这里被盗墓分子盗掘。
晋侯墓地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1992年初春,邹衡前往曲村考古工作站。途经太原时,听说1991年腊月间,在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村曾有大规模的盗掘事件发生。据传,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挖出许多“宝物”,到曲村后不久又不断听到类似的消息,这引起了邹衡的警觉。
在调查过程中,邹衡和考古专家分析被盗墓地现场,结论既令人痛心又惊叹难言。经现场勘查和询问,得知被盗墓地挖掘出大量大型青铜器,盗墓分子的恶劣行径令人痛恨,而大量青铜碎片和墓葬的格式,正印证了邹衡追寻十几年的晋侯墓地。
1992年,抢救性发掘开始了,从1992年到2007年,大型考古发掘共9次,晋侯墓地的大门被打开,共有晋侯夫妇墓9组19座,车马坑10座,陪葬坑、祭祀坑各几十座。其中晋侯夫妇墓被盗8座,陪葬墓被盗9座。苦苦寻找的“晋国踪迹”原来就在身边,考古人员没有发现,反倒是盗墓贼先打开了大门。或许这是那个时代的困局:考古发掘引来盗墓贼,而盗墓又指引了考古发掘的方向。田建文回忆说,那些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有一半以上都是盗墓贼盗墓后开始的抢救性发掘。
1995年3月至6月,山西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春季“严打”斗争,晋侯墓地被盗案中,36名不法分子被逮捕,包庇、参与其中的政府官员被依法处理,10名罪犯被枪决,成为当时的“文保第一案”,恶性盗掘才被遏制。1998年,曲沃县文物局起草并以县政府名义给省政府写过一个《关于建立晋侯墓地遗址博物馆》的报告,2008年9月30日晋国博物馆项目在省发改委正式立项,2009年8月31日晋国博物馆正式动工兴建。
本报记者 刘斌
(原标题:半个多世纪发掘 从寂寂无闻到风起云涌)
[新浪网-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