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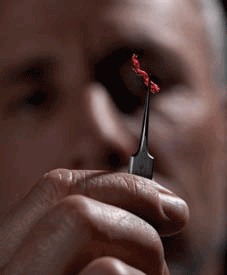
犯罪现场调查
撰文 马克思·霍克(Max Houck)
法证类电视节目中,神奇的法证技术让人们赞叹不已;潇洒自信、无所不能的调查人员让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证科学家们拥有的,更多的是无奈……
从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杜宾冒险故事,到阿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 Conan Doyle)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传奇,再到杰克·克卢格曼
(Jack Klugman)的电视系列剧“验尸官昆西(Quincy)”,法证科学(Forensic science)从来都是这些传奇故事的主线。福尔摩斯使用了多种现代法证技术,例如血液检测,正是这些技术的使用,才使罪犯的滔天恶行大白于天下。早在百年前,法证科学就被系统地整理成一门专业,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DNA分析技术的出现,人们才突然意识到,法证科学来了!
法证科学从未如此深入人心:2005年10月,八部罪案剧,包括《CSI:犯罪现场调查》及其姊妹剧,全都挤进了电视节目收视排行榜的前20位。就在当月的一个星期四,美国有27%的电视机都在播放CSI类节目。在有线电视方面,法庭电视台(CourtTV)播出了一部描述真实罪案和真实科学家的纪录片风格的系列剧——法证档案(Forensic Files),每周播出四天。这类节目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法证实验室的人员充足、训练有素,设备尖端、配套完整,善于分析,破案神速。
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与现实之间,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CSI节目盛行,已经导致了“CSI效应”,部分律师和法官对此颇有微词:自从2000年CSI开播以来,陪审员深受影响,在审判过程中,他们对物证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CSI效应真对法庭的判决产生了可计量的影响?没人敢妄下结论。不过, CSI节目产生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这一点,不容置疑:警察办案时,他们会争取收集更多的物证;在学术界,法证课程呈指数倍增长;超负荷运转的实验室也难以幸免,尽管它们与传说中的分析天堂相去甚远。
法庭上的CSI效应
本季CSI的某一集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在虚构犯罪现场,一个电视摄制组正在记录调查员的活动。调查组主管吉尔·葛里森(Gil Grissom)出面干涉摄制组的行为,并说道:“电视上的法证节目已经泛滥成灾了。” 这句话可能是众多律师和法官共同的心声,因为他们认为,陪审员已经深受CSI效应的影响。那么,CSI类节目对陪审员的判案心理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2003年,新闻媒体开始关注“CSI效应”。他们从律师和法官那里收集了一些奇闻轶事,这些趣闻似乎说明,陪审员的态度正在悄悄地改变。2005年,俄勒冈州的地方检查官、美国全国检察官协会(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副主席,乔希·马奎斯(Josh Marquis)在CBS新闻中说:“现在,陪审员们的期望值不断升高,他们要求我们对每一起案件都做DNA检测、尽可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甚至要与电视中的技术一样神奇。”在审判发生在洛杉矶的一起谋杀案时,陪审员报怨说,有一件血衣没有经过DNA检测,尽管根本没有必要——被告人已经承认自己曾经去过案发现场。马奎斯说,陪审员只从电视上了解了何为DNA检测,却不知何时使用DNA检测。在特拉华州,曾开设过一次研讨班,主要培训陪审员如何处理物证。课上,复杂的DNA案例让一位陪审员晕头转向。于是,这位老兄开始报怨了:在CSI中,绝不会有如此复杂的东西。
在审判巴尔的摩的一起谋杀案时,面对两位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词,陪审团熟视无睹,执意宣告凶手无罪。而理由竟是,物证不足!律师们认为,这就是“CSI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过去五年间,陪审员和他们的期望值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算是见识了‘CSI效应’的威力,”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辩护律师约瑟夫·列文(Joseph Levin)对当地一家报纸这样说道,“在审议时,如果陪审员没有看到想要的证据,他们就会问法官,罪犯的指纹或DNA在哪里?如果法官说没有,他们还会问,为什么会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明星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杀妻案曾轰动一时。在该案的审判过程中,起诉人不仅陈述了布莱克的杀人动机和时机,还传唤了证人,指认布莱克曾经要求证人谋杀他的妻子。不过,这些没能让陪审团信服,原因只有一个:起诉人无法提供枪击残留物(gunshot residue)和血迹(blood spatter)证据。最后,布莱克无罪释放。当时,一位陪审员是这样说的,如果起诉人“掌握了所有物证资料,那才意味着(布莱克)有罪”。 在前49起谋杀案中,这位起诉人未尝败绩。这一次,他不得不败走麦城。
在CSI普及之前,律师通常会担心,陪审团能否理解复杂的DNA证据;而现在,律师却要花时间澄清电视节目与现实的不同。“请问陪审团成员,你们是否看过法证类电视节目?”这句话几乎已成为律师们的开场白。为了避免CSI效应带来的影响,一些起诉人殚精竭虑。在亚利桑那、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反证证人(negative evidence witnesses)”已经走进法庭、坐上证人席。他们的作用是提醒陪审员:现实生活中,警察也是人,要在犯罪现场找到DNA或者指纹,并不容易。
但是,有几位法学专家认为,CSI效应纯属胡扯。援引列文律师原话的那家报纸,还刊登了高等法院法官艾伯特·加罗佛罗(Albert Garofolo)的原话:“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没错,CSI效应的确存在’。不过,现在我认为,这只是大家妄加猜测。我确实感觉到CSI效应可能存在,可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陪审员说过,他们想看到更多证据。”
2005年,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犯罪、法律与社会学系的西蒙·科尔(Simon Cole)和他的学生雷切尔·迪奥索(Rachel Dioso)写道:“电视或许能影响法庭的判决,这并非不合情理……不过,非要说‘CSI’类节目提高了无罪裁决的频率,这就有点骇人听闻。重要的是,从法证科学的角度来说,根本没有丝毫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以陪审团的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多如牛毛,但没有任何项目找到了CSI效应存在的证据。唯一算证据的,只是一些奇闻轶事罢了。”
在千呼万唤中,对CSI效应的首项研究终于出现了。2006年2月,金伯里安妮·波德拉斯(Kimberlianne Podlas)公开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波德拉斯既是律师,又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绿乡分校新闻法规与道德学的副教授。她认为,对于CSI的忠实观众和从未看过这些节目的陪审员来说,无罪裁决的几率和原因并无差异——她没有看到任何CSI效应。不过,几位受试者曾说,不对物证进行法证检验不能让人信服,尽管这些物证对案情的进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对货真价实的陪审员进行研究已经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并且至少有五名研究生(三人在美国,两人在英国)正在为研究做相关准备。
事实真相
不管法证类节目是否对陪审团的要求和裁决产生了可计量的影响,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电视节目正在向观众传播歪曲的观念,例如法证科学如何操作、哪些可以做到、哪些无法做到。在电视剧中,扮演法证人员的演员被刻画成了警察、侦探与法证科学家三位一体,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超人”。执法、调查和法证科学是三项独立的职业,每一项都极其复杂,需要工作人员接受专门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专门的技能。此外,法证实验室中的专业划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一项规范。每一位法证科学家都必须对其他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不过,没有人能精通与犯罪现场调查有关的所有专业。
另外,或由于经费紧张,或由于资源不足,或由于无人要求,法证实验室一般不会对物证进行全项分析。电视节目错误地描绘了法证科学家:他们时间充裕,足以应对每一起案件;电视中的侦探、技术员以及科学家经常全身心地投入一项调查之中。而现实生活中,科学家们任务繁重,通常会接到多起案件。在大部分法证实验室,案件堆积如山,未完结的案件已成为工作人员的心病。为了处理数不胜数的案件,实验室不得不申请更多的经费。
在描述法证技术时,虚构的法证节目也常常脱离现实: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法证科学家托马斯·毛里耶罗(Thomas Mauriello)估计,在CSI节目展示过的技术中,约有40%是不存在的。卡罗尔·亨德森(Carol Henderson)是美国斯特森大学法学院国家科技及法律情报交换所(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Law)的主席,他对交换所的一份刊物说,陪审员“有时会感到失望,假如他们认为本来存在的技术而未被使用的话”。同样,电视中的调查人员可能会让现实中的同仁“自惭形秽”。电视上,一个调查员把一种未知的样品,拿到一台仪器上进行分析,几束光线闪烁之后,荧光屏上输出了结果——“美宝莲口红,42#色,批号A-439”。接下来,他就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询问嫌疑人:“我们知道受害者跟你在一起,因为在你的衣领上,我们鉴别出了她的口红。”在现实生活中,答案很少会如此明朗,调查人员也不会与嫌疑人正面接触。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会产生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市的一位警官说:“我遇到了一位汽车抢劫案的受害者,他在自己的汽车尾部发现了一根红色纤维。他说,他想让我做个检测,弄清出这根纤维打哪儿来,罪犯是在哪一间零售商店购买的,用的哪一张信用卡付账。”
难以承受之重
尽管法证科学家的装备无法与电视中的相媲美,但他们确实拥有一些先进的、不断完善中的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初级的DNA检测方法需要一夸特的血液样品,而现在,仅需几纳克(nanogram)样品就足够了。利用先进的法证技术,可以侦破旧案、扫除嫌疑、推翻错判。在电视上,这类新闻层出不穷。DNA、指纹和枪械弹药数据库已经变成了重要的资源,可以将罪犯与多宗罪案联系起来。
然而,与电视剧中轻松创造奇迹相比,现实生活中的实验室更像是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分析申请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由于警方调查人员知道科学分析的好处,同时也迫于收集更多证据的压力,他们正从更多的案件中,提交更多的证物,以供法证分析之用。过去,警察从一个犯罪现场收集的证据也许只有5件,但是现在,他们会收集50到400件。1989年,弗吉尼亚实验室只处理了几十起案件。而今年,他们手头的案件已经暴涨到几千起。当然,并不是犯罪现场的每一件物品都可以,或者应该拿来做检测。面对繁重的物证分析任务,法证科学家不得不作出取舍,挑出最有可能成为重要证据的物品进行检测。但是,电视节目让人们的期望值升高,甚至不切实际,这给法证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自社会、来自职业本身、来自政治领域。因此,假如一位警察带回了满满一大袋啤酒罐、烟屁股、速食包装袋和其他垃圾的话,那么迫于压力,大部分物品都很有可能进入检测计划。
在许多案件中,不堪重负的法证人员不得不继续承担所有的分析工作。例如,在波士顿市以外,马萨诸塞州拥有630万人口,而负责这一地区的DNA分析员只有8名(波士顿市还有3名)。纽约市的人口略多(800万),他们配备了80名DNA分析员。但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市的暴力犯罪率却相差无几(分别是每100,000人469.4起和483.3起)。处理这类案件时,DNA证据异常重要。因此,与其他很多州一样,马萨诸塞州的DNA分析员明显偏少。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同意招聘更多的DNA分析员。
随着物证采集数量的激增,本来就让法证实验室头痛不已的案件积压问题日益加剧。最近,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根据最新的可用数据),截止2002年底,超过50万起案件被积压在法证实验室,尽管物证检测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完成率的90%。这项研究估计,如果当年要有30天的周转时间,实验室就得另外聘请1,900位全职雇员。司法部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2002年,美国50个最大的法证实验室接到的法证检测申请超过了120万份:在一年内,这些实验室积压的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这些增长还是在1994年以来犯罪率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
物证采集数量增加的另一个恶果,就是物证的储存问题。地方、州市以及联邦政府的法规各异,因而物证的储存年限也各不相同。储存证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计算机、软件和人员来查询证据;需要专用设备来安全地储存生物学证据,例如DNA;需要足够大的仓储空间来容纳物证。在许多法域(jurisdiction,具有自己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储存超过一定年限的证据可能会被销毁或返还。对于一些旧案或陈案来说,物证的存储至关重要——美国纽约市卡多佐法学院的无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 at Cardozo Law School in New York City)已经发现,在他们深入调查的、有可能存在误判的案件中,有75%的案件,它们的证据已经不见踪影。
就算是追查确实存在的证据也是问题重重。2003年,美国罪案实验室主管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rime Laboratory Directors)作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全美超过1/4的法证实验室根本没有配备必需的计算机以记录证据的去向。美国奥尔巴尼大学东北地区法证研究所(the Northeast Regional Forensic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any)所长、纽约警察局实验室(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Laboratory)前主管马克·戴尔(Mark Dale)估计,想要在以后十年里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就得另外聘请10,000名以上的法证科学家。此外,设备的更新换代将花费13亿美元,添置新设备也将需要投入超过2.85亿美元的资金。
[环球科学]